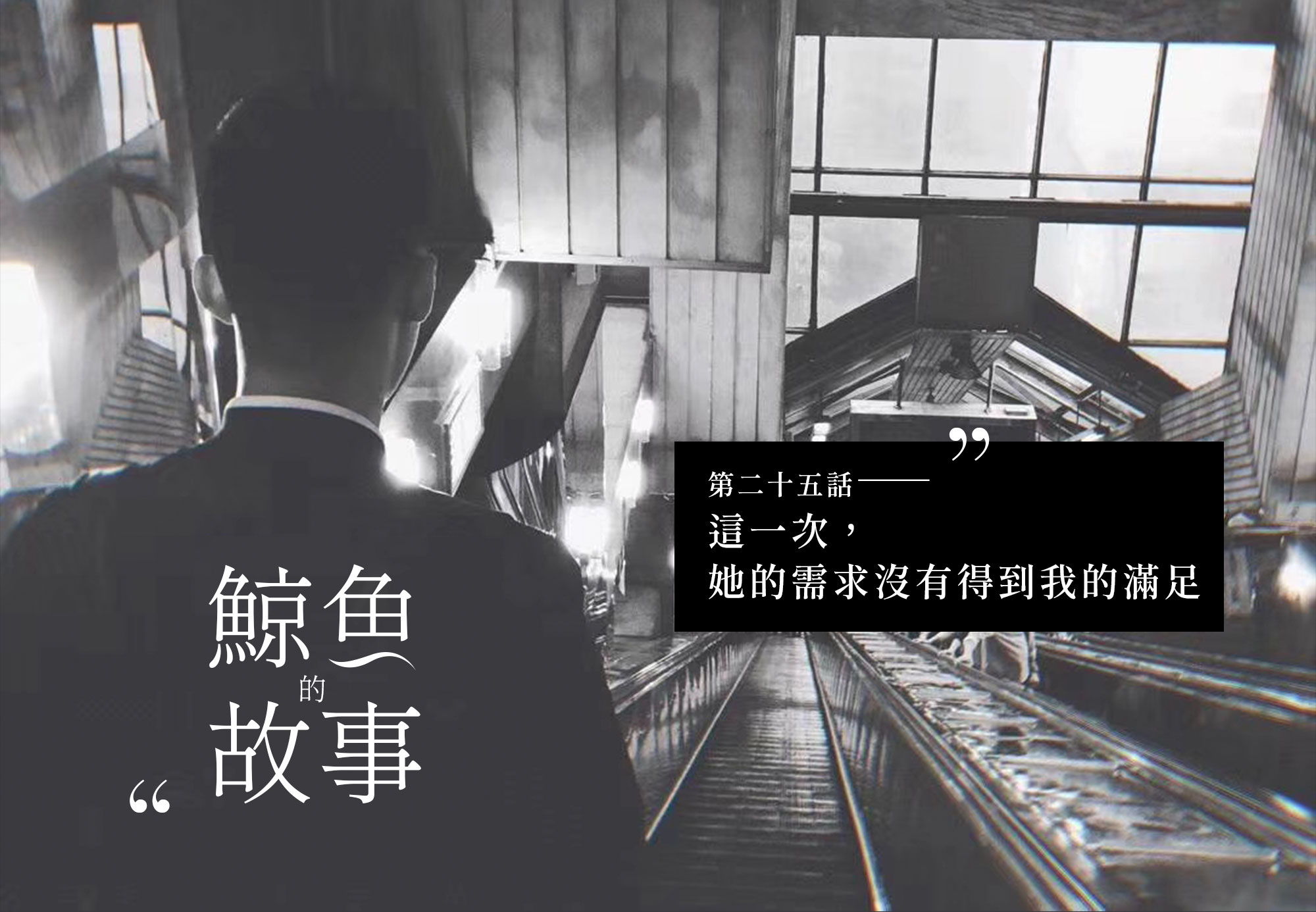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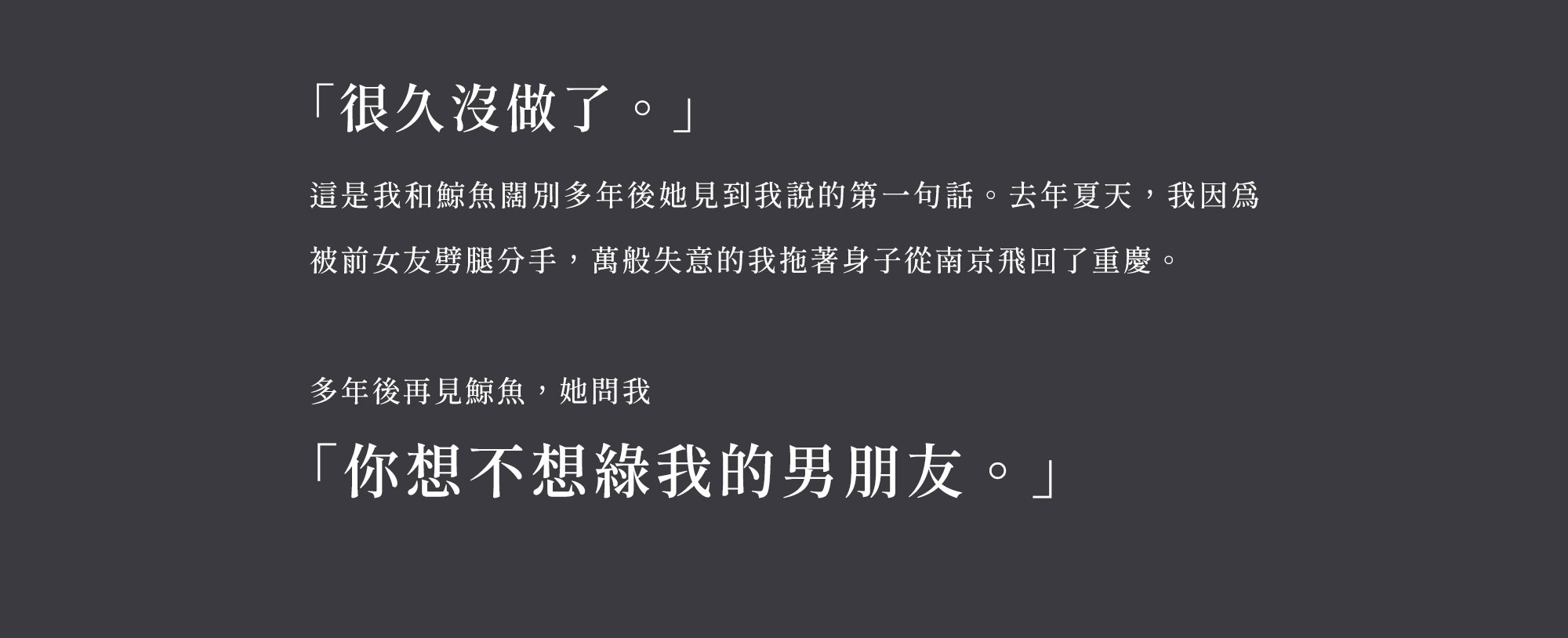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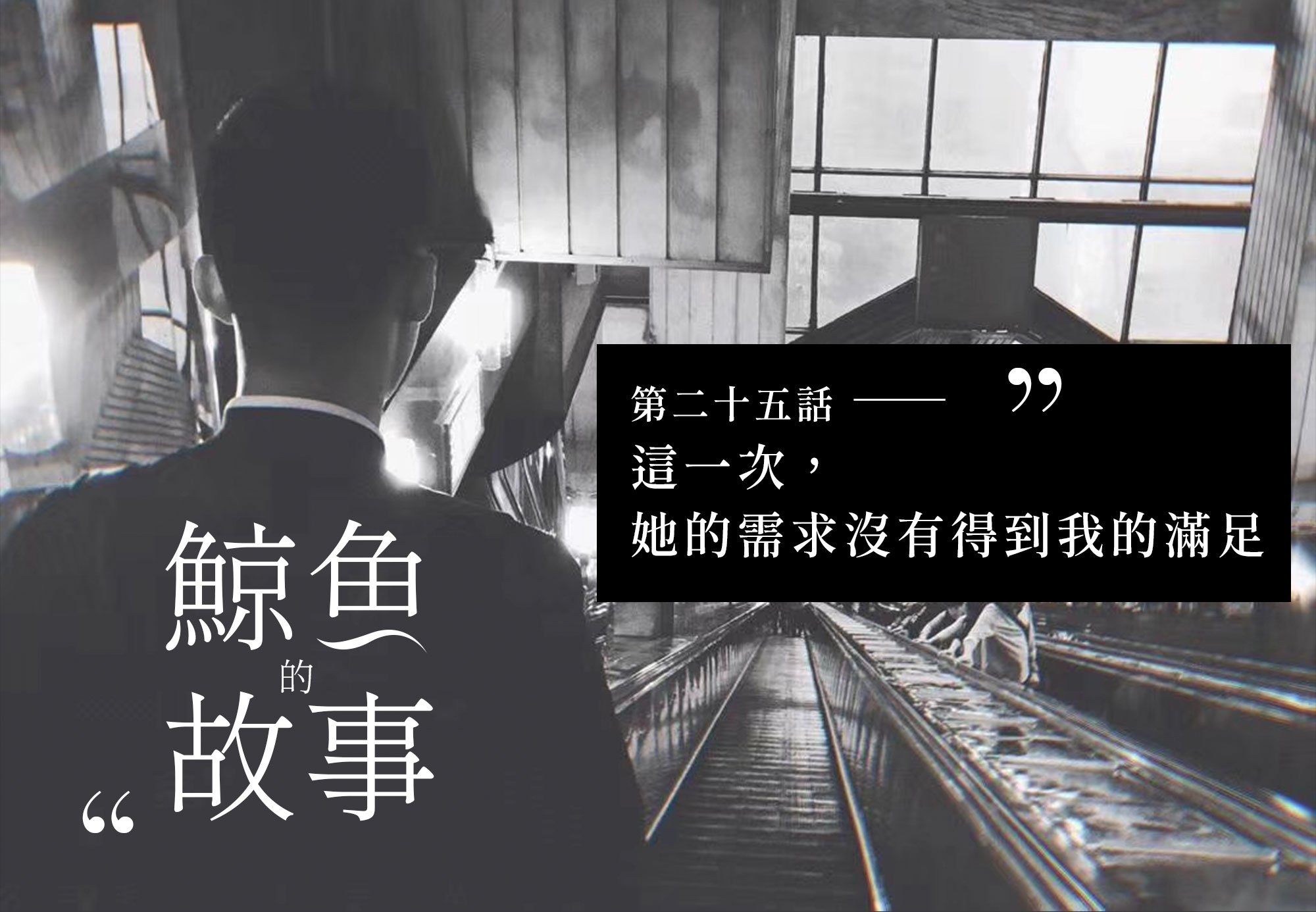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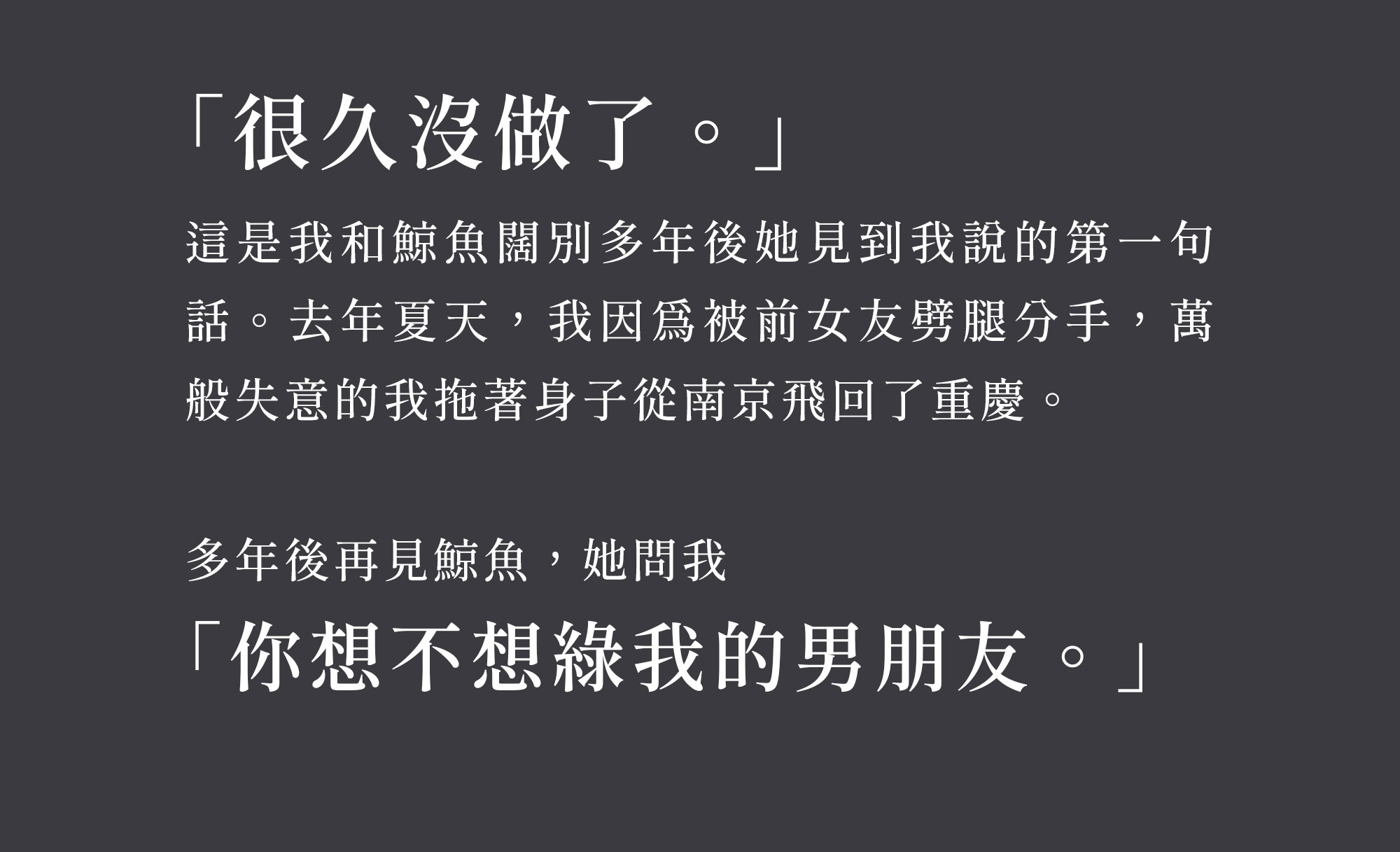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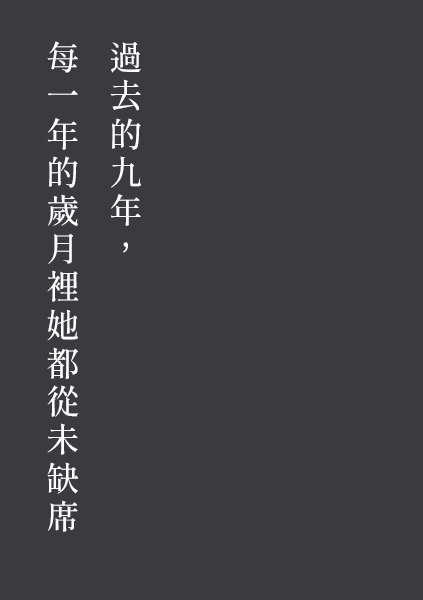
時間一晃就到了2020年的年底,窗外的冷空氣讓我恍惚覺得此刻還是今年剛開年的時候,我正窩在家裡因為新冠隔離,沒事就和鯨魚一起打打遊戲。仔細算算,我和鯨魚已經認識了整整9年。過去的9年,每一年的歲月裡她都從未缺席,像是候鳥一樣,每一年都會飛到我身邊過冬,但是每一年都總會飛走。
回到正題,自打和鯨魚在她家裡革命友誼之後,鯨魚的假期也到了尾聲,在這之前我們一起計畫了一次短途旅行。起因還是因為鯨魚在抖音上刷到一個在重慶很美的盤山公路。兩側是翠綠的長江,泊油路邊是鬱鬱蔥蔥的草坪,路上還有奶白色的風力發電機。想著近來無事,便應允了和鯨魚的這次短途旅行。打開地圖搜索了一下這個位置,整整兩百多公里的路程,只能驅車前往。
出發的那天,汽車行駛在高速上的時候,鯨魚沒怎麼說話,她用手機連接著車上的藍牙音箱,車裡一直迴響著 Eleni Karaindrou 的靡靡之音。
她說她有點累了,想要睡一會。我說你把座椅放下來睡一會吧,到了之後我叫你。鯨魚點點頭,越過中控台在我臉上輕輕啄了一口。我開玩笑說,高速路上別整這一出啊,等會拍到了我可沒分給你扣啊。她笑了笑,又啄了一下說,那扣我的。然後就放下座椅開始休息。我側過頭看了一眼鯨魚閉眼的樣子,睫毛撲朔,像一隻小獸一樣。我順手把音量調到最低,順著公路疾馳而去。
我們到目的地的時候已經快接近黃昏,鯨魚在副駕上已經睡得安穩,我放慢速度停好車,沒有叫醒她。只是望著窗外的景色發呆。過了一小會,鯨魚睜開睡眼惺忪的雙眼,伸了一個懶腰,問我到哪兒了,為什麼停下來了。
我無辜的看著她說,「遭了,汽車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壞掉了,我們今天去不成了,我剛給高速打了電話,他們會帶拖車過來。」
鯨魚皺皺眉說,「怎麼可能啊。這車不是才保養過的嗎?」,說著就要下車去查看。
她推開門之後,看著遠處三五成群的風車,以及緩緩下墜的夕陽時才反應過來我是在逗她。我在車裡看著她笑,她招招手讓我出去。我們的車停在靠近江邊的一個寬廣的路面上,鯨魚站在江邊,晚風吹著她的白色紗裙的裙擺,夕陽映襯著她的臉,顯得特別好看。
我站到她身後,她沒有回頭看我。輕輕的對我說,「抱我。」
我說,「什麼?」
她說,「從背後抱著我。」
我聽後將手慢慢環繞過她的腰間,把腦袋倚在她的耳邊。鯨魚用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兩個人都沒有說話,甚至沒有眼神上的交流。我能聽見江水緩緩流淌而過的拍打兩岸的聲音,垂垂老矣的夕陽給天邊抹上了一道橘黃。鯨魚把頭像小貓一樣在我的臉上蹭了蹭。
她說,「要是時間可以一直暫停在這一刻,那該有多好呀。」
我沒有做聲,只是把她抱得更緊了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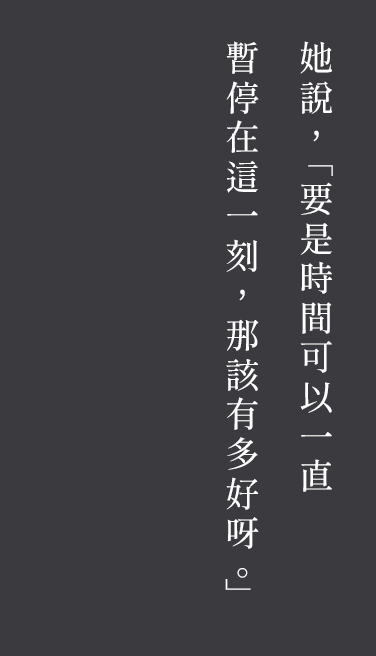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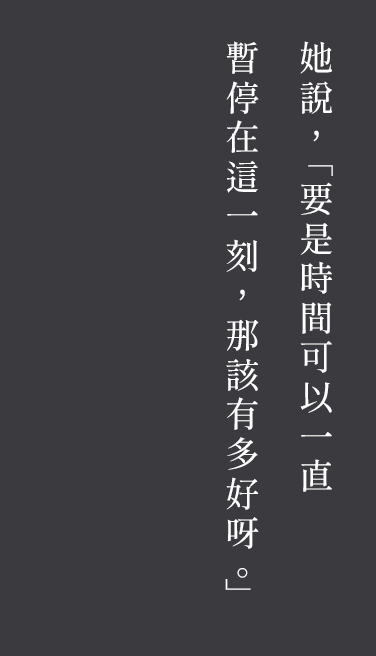
我無辜的看著她說,「遭了,汽車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壞掉了,我們今天去不成了,我剛給高速打了電話,他們會帶拖車過來。」
鯨魚皺皺眉說,「怎麼可能啊。這車不是才保養過的嗎?」,說著就要下車去查看。
她推開門之後,看著遠處三五成群的風車,以及緩緩下墜的夕陽時才反應過來我是在逗她。我在車裡看著她笑,她招招手讓我出去。我們的車停在靠近江邊的一個寬廣的路面上,鯨魚站在江邊,晚風吹著她的白色紗裙的裙擺,夕陽映襯著她的臉,顯得特別好看。
我站到她身後,她沒有回頭看我。輕輕的對我說,「抱我。」
我說,「什麼?」
她說,「從背後抱著我。」
我聽後將手慢慢環繞過她的腰間,把腦袋倚在她的耳邊。鯨魚用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兩個人都沒有說話,甚至沒有眼神上的交流。我能聽見江水緩緩流淌而過的拍打兩岸的聲音,垂垂老矣的夕陽給天邊抹上了一道橘黃。鯨魚把頭像小貓一樣在我的臉上蹭了蹭。
她說,「要是時間可以一直暫停在這一刻,那該有多好呀。」
我沒有做聲,只是把她抱得更緊了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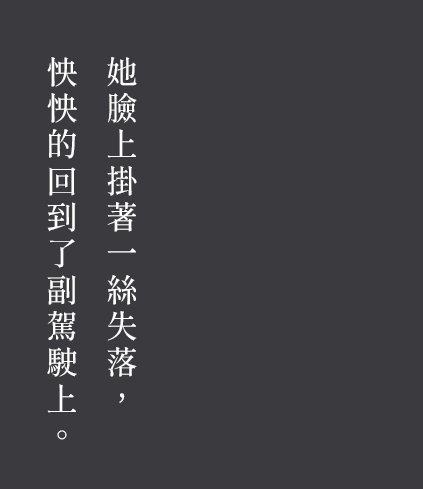
天色漸暗,初秋的風已經有了些許的涼意,我讓鯨魚回到車裡。她徑直打開了後排的車門,我說,「你坐到後面去幹嘛?」
鯨魚示意我也到後排裡,有事要給我講。我沒有問為什麼,這是我和鯨魚多年以來形成的默契。落座到後排的時候,鯨魚輕輕解開了裙子背後的拉鍊,露出了光潔雪白的肩膀,想要索吻。可是我已經被一路上的奔波搞得很疲憊,讓我提不起來興致。我象徵性的回應了她一個吻,捧著她的臉說,「乖,天快黑了。」,然後給她拉好拉鍊,坐回到了駕駛室裡。
也許是第一次訴求沒有得到滿足,也可能是鯨魚沒有想到我會拒絕她。她臉上掛著一絲失落,怏怏的回到了副駕駛上。她感覺她的魅力在我這裡開始衰敗得不到回應。
汽車行駛在盤山公路上的時候,鯨魚打開了車窗,她側著臉看著漆黑的窗外,從山腰外灌進來的陣陣涼風讓我覺得有些涼意。鯨魚點了一支煙,遞到我的嘴邊,我很自然地接住。我注意到她的神色有一些不開心,低聲問她怎麼了。鯨魚沒有回應我的話。
車裡昏暗的燈光打在她神色黯淡的臉上,讓她看起來有些陌生。我從來沒有見過鯨魚的這一副表情,加上一整天我們幾乎都沒有怎麼溝通,汽車內的氣氛一時間有一點令人窒息。
路燈一盞盞劃過的時候,音響恰好播放到《California dreaming》,那個瞬間我不知道為什麼回想起周驚蟄,我想起我和她第一次坐在長途大巴上從重慶去成都的畫面。那天也是這樣昏黃的燈光,也是同樣的一首歌。第一次覺得物是人非。想著想著,不由發出來一聲歎息。
鯨魚見我一直沒有說話,本來不開心的臉上又增添了幾絲嗔怒。她首先開口說,「我不知道你什麼意思,既然這麼不想出來你就不要答應我。本來我精心策劃了一晚上,結果沒有想到你是這種態度。」
我覺得很無辜,因為大半天的駕駛已經將我的精力消耗殆盡。我絲毫沒有和鯨魚爭論的心思,也沒有多做解釋。鯨魚見我沒有說話,變得更加的生氣起來。原本設想中的浪漫出行竟然隱隱有了要開始爭吵的趨勢。我忽然覺得這時候的鯨魚,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體貼懂事,她其實和大多數女人一樣,關注點從來都是在自身,對自我的過多關注,希望她身邊的男人也把注意力都放在她的身上,總是希望在異性身上得到肯定和讚美,一旦沒有得到回應,就開始各種設想,然後開始追問和考驗,直到那個男人喘不過氣來為止。不出意外的話,鯨魚下一個問題一定是會問我到底喜不喜歡她。
果不其然,在沉默了半晌之後,鯨魚朱唇輕啟,她轉過頭看著我很久才認真的問到,「我問你,你真的喜歡我嗎?」
雖然在意料之中,但是這個問題還是讓我覺得很心煩。夜裡的上路上已經一輛車都見不到了,鯨魚抱著雙臂拉著臉直視著我,看起來如果我不回答她這個問題她今天非得和我無理取鬧不可。於是我覺得服服軟,我擠出一個微笑說,「哪有的事,你不要亂想了。」,沒想到我的這番回答無異於火上澆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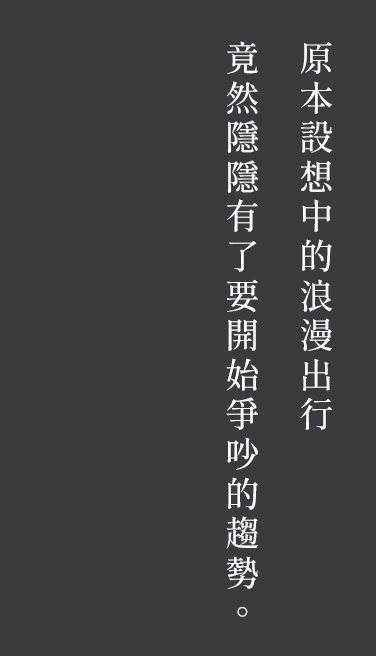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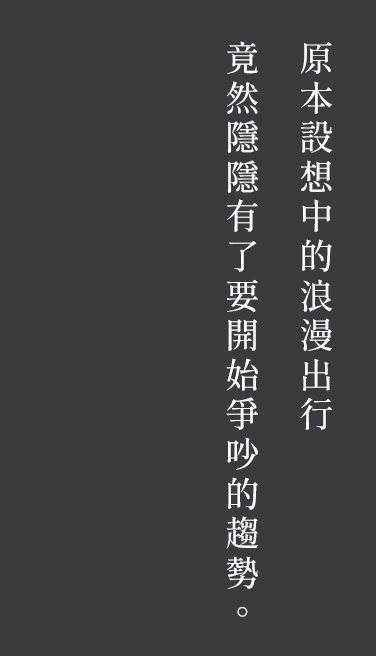
路燈一盞盞劃過的時候,音響恰好播放到《California dreaming》,那個瞬間我不知道為什麼回想起周驚蟄,我想起我和她第一次坐在長途大巴上從重慶去成都的畫面。那天也是這樣昏黃的燈光,也是同樣的一首歌。第一次覺得物是人非。想著想著,不由發出來一聲歎息。
鯨魚見我一直沒有說話,本來不開心的臉上又增添了幾絲嗔怒。她首先開口說,「我不知道你什麼意思,既然這麼不想出來你就不要答應我。本來我精心策劃了一晚上,結果沒有想到你是這種態度。」
我覺得很無辜,因為大半天的駕駛已經將我的精力消耗殆盡。我絲毫沒有和鯨魚爭論的心思,也沒有多做解釋。鯨魚見我沒有說話,變得更加的生氣起來。原本設想中的浪漫出行竟然隱隱有了要開始爭吵的趨勢。我忽然覺得這時候的鯨魚,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體貼懂事,她其實和大多數女人一樣,關注點從來都是在自身,對自我的過多關注,希望她身邊的男人也把注意力都放在她的身上,總是希望在異性身上得到肯定和讚美,一旦沒有得到回應,就開始各種設想,然後開始追問和考驗,直到那個男人喘不過氣來為止。不出意外的話,鯨魚下一個問題一定是會問我到底喜不喜歡她。
果不其然,在沉默了半晌之後,鯨魚朱唇輕啟,她轉過頭看著我很久才認真的問到,「我問你,你真的喜歡我嗎?」
雖然在意料之中,但是這個問題還是讓我覺得很心煩。夜裡的上路上已經一輛車都見不到了,鯨魚抱著雙臂拉著臉直視著我,看起來如果我不回答她這個問題她今天非得和我無理取鬧不可。於是我覺得服服軟,我擠出一個微笑說,「哪有的事,你不要亂想了。」,沒想到我的這番回答無異於火上澆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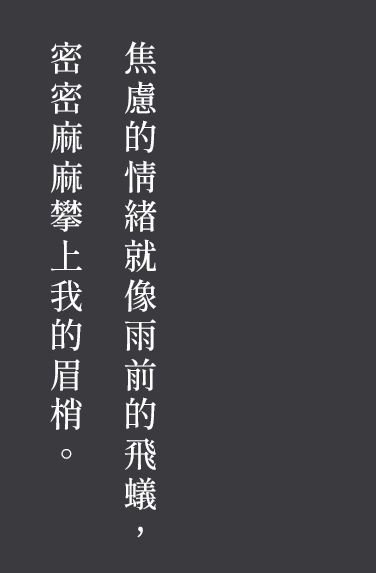
鯨魚不再做聲,她面無表情的看著前方黑漆漆的路,開始用沉默抗議。我接連試探了她好幾次她都不肯開口。
我開始哄她,我說,「魚兒,今天我們去哪裡啊?」
她不說話。
我又說,「魚兒你一天沒吃東西,你要不要看看附近有沒有什麼吃的地方。」
她依然不說話。
我耐著性子又問她,「你冷嗎?要不要把後面的毯子披上。」
這一次她終於說話了,她語氣平淡的說,「不要和我講話,煩死了。」
我終於被她的無理取鬧搞得徹底沒了興致,於是我也不再和她講話,任由車子沿著公路漫無目的的往前一直開。
車子在漆黑的山路上緩緩而行,慘白的燈火穿過松林,驚起一群小獸。放在以前,鯨魚一定會歡呼雀躍地問我那是什麼動物,然後等我說道。可是她此時沉悶得像夏季暴雨前的烏雲,越是這種沉默越讓我焦慮,焦慮的情緒就像雨前的飛蟻,密密麻麻攀上我的眉梢。
我討厭無休止的冷戰,我寧願她忽然大吵一架。可是我們的性格又太相似了,誰也不想打破這種沉默。我以為冷戰是男人的專屬,可是回到女人的手裡卻又是堅韌的利器。我有時候實在不懂為什麼女人那麼愛生氣,沒有來由也沒有一個生氣的終點。任憑你去想去猜,可到頭來她給你來一句:「我要的是你的態度。」
此時的鯨魚讓我覺得有點陌生,我回想起那年的盛夏,在江邊露臺的酒店落地窗前的瞬間。我想到那晚窗戶外面閃爍的霓虹映襯在她姣好又青春的側臉上,她微微捲曲的褐色頭髮散落在她光潔的背。我坐在她對面的沙發上,她背對著窗戶沖我微笑。我說要不要加點音樂,她就播放了 The marias 的《i like it》。
彼時還充滿著熟悉又陌生的驚喜,我看著她閃爍的雙眼,就可以有無聲的對話。我很享受那段時光,她緩緩走過來,解開吊帶襪的活扣,頭髮散落在我的臉上,她獨特又熟悉的味道散漫開來。
我永遠記得和她度過的那個夏季,我覺得我身邊的這個女人,濕滑嬌嫩的身體不是一具簡單的軀體,更像是一件藝術品。它包含著萬縷愛意和粘稠熾熱的液體,奔湧不息。
這種感覺很久都沒有再體會過了。
想到這些美好瞬間,我忽然覺心軟。我按下車窗,山風擁擠進狹窄的車裡,打破了壓抑的寧靜。我用手指敲了敲方向盤,低聲問鯨魚:「魚兒,你肚子餓不餓。」,沒有轉過頭看她。她沒有回應,迎接來的是數十秒的沉默。
我又擠出一點笑意說:「魚兒,我肚肚餓了。」
我透過內後視鏡瞥了她一眼,她嘟著嘴,表情稍有緩和。半晌,終於擠出一句:「餓死算了,餓死了才沒有人氣我。」
當她說出這種話的時候,我知道她氣也消得八九不離十了。我說,「你看這荒郊野嶺的,又沒有飯店,也沒有酒店,我們吃什麼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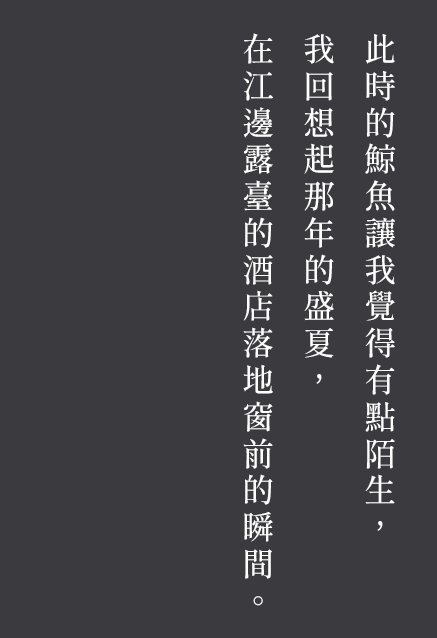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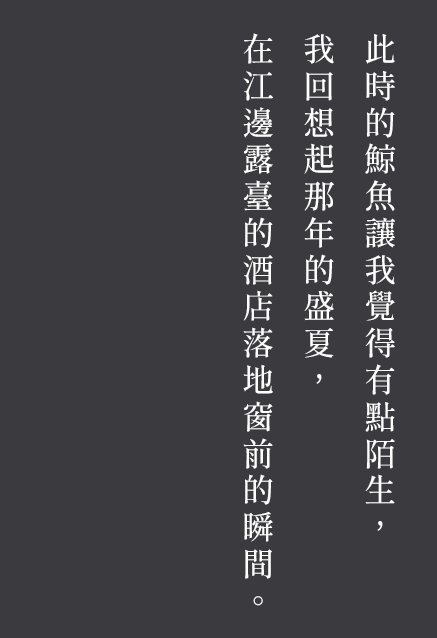
此時的鯨魚讓我覺得有點陌生,我回想起那年的盛夏,在江邊露臺的酒店落地窗前的瞬間。我想到那晚窗戶外面閃爍的霓虹映襯在她姣好又青春的側臉上,她微微捲曲的褐色頭髮散落在她光潔的背。我坐在她對面的沙發上,她背對著窗戶沖我微笑。我說要不要加點音樂,她就播放了 The marias 的《i like it》。
彼時還充滿著熟悉又陌生的驚喜,我看著她閃爍的雙眼,就可以有無聲的對話。我很享受那段時光,她緩緩走過來,解開吊帶襪的活扣,頭髮散落在我的臉上,她獨特又熟悉的味道散漫開來。
我永遠記得和她度過的那個夏季,我覺得我身邊的這個女人,濕滑嬌嫩的身體不是一具簡單的軀體,更像是一件藝術品。它包含著萬縷愛意和粘稠熾熱的液體,奔湧不息。
這種感覺很久都沒有再體會過了。
想到這些美好瞬間,我忽然覺心軟。我按下車窗,山風擁擠進狹窄的車裡,打破了壓抑的寧靜。我用手指敲了敲方向盤,低聲問鯨魚:「魚兒,你肚子餓不餓。」,沒有轉過頭看她。她沒有回應,迎接來的是數十秒的沉默。
我又擠出一點笑意說:「魚兒,我肚肚餓了。」
我透過內後視鏡瞥了她一眼,她嘟著嘴,表情稍有緩和。半晌,終於擠出一句:「餓死算了,餓死了才沒有人氣我。」
當她說出這種話的時候,我知道她氣也消得八九不離十了。我說,「你看這荒郊野嶺的,又沒有飯店,也沒有酒店,我們吃什麼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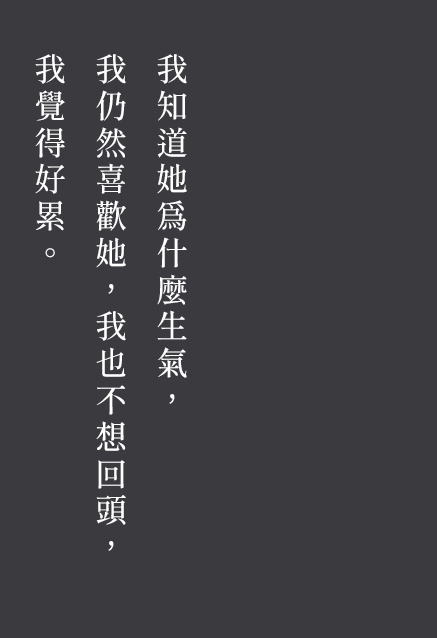
鯨魚以為我在抱怨,她忽然話音轉變,她說,「你出門都不看的嗎?我們剛剛在山下就該停車的。你自己非要往上面開。」
我說,「那你知道該停車你怎麼不說。」
她說,「我懶得說。」
我最後的好脾氣被她這喜怒無常的變化消耗殆盡,我踩下刹車,鯨魚往前傾了一下,回頭對我說了句,「你有病啊?」
我打開車門走出去說,「對啊,我有病。」
這個時候她可能意識到自己任性讓我生氣,沒有生氣也沒有再耍脾氣,只是怯生生的也走出車門低著頭站在路邊。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的鯨魚和我記憶中所有瞬間的鯨魚都沒有辦法聯繫起來,很陌生。我看著她依然姣好美麗的臉,眼眶紅紅的,半咬著嘴唇看著我,可是我竟然沒有半點心軟,我覺得這個她才是真實的她,她那些所有歲月靜好的樣子,都是另一個她。
我淡淡的用只有我們兩個聽到的聲音對她說,「你自己開車回去吧,不用管我了。」,然後自顧自的往山下走去。
鯨魚叫了我兩聲,我沒有回頭,走了很遠。她開始打過來電話,我沒有接。電話接踵而至,我索性關掉了手機。從山腰傳來了陣陣汽車鳴笛的聲音,驚起無數飛鳥。我知道她為什麼生氣,我仍然喜歡她,我也不想回頭,我覺得好累。
閲讀前文
Art Design: Vickey
